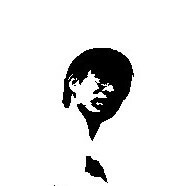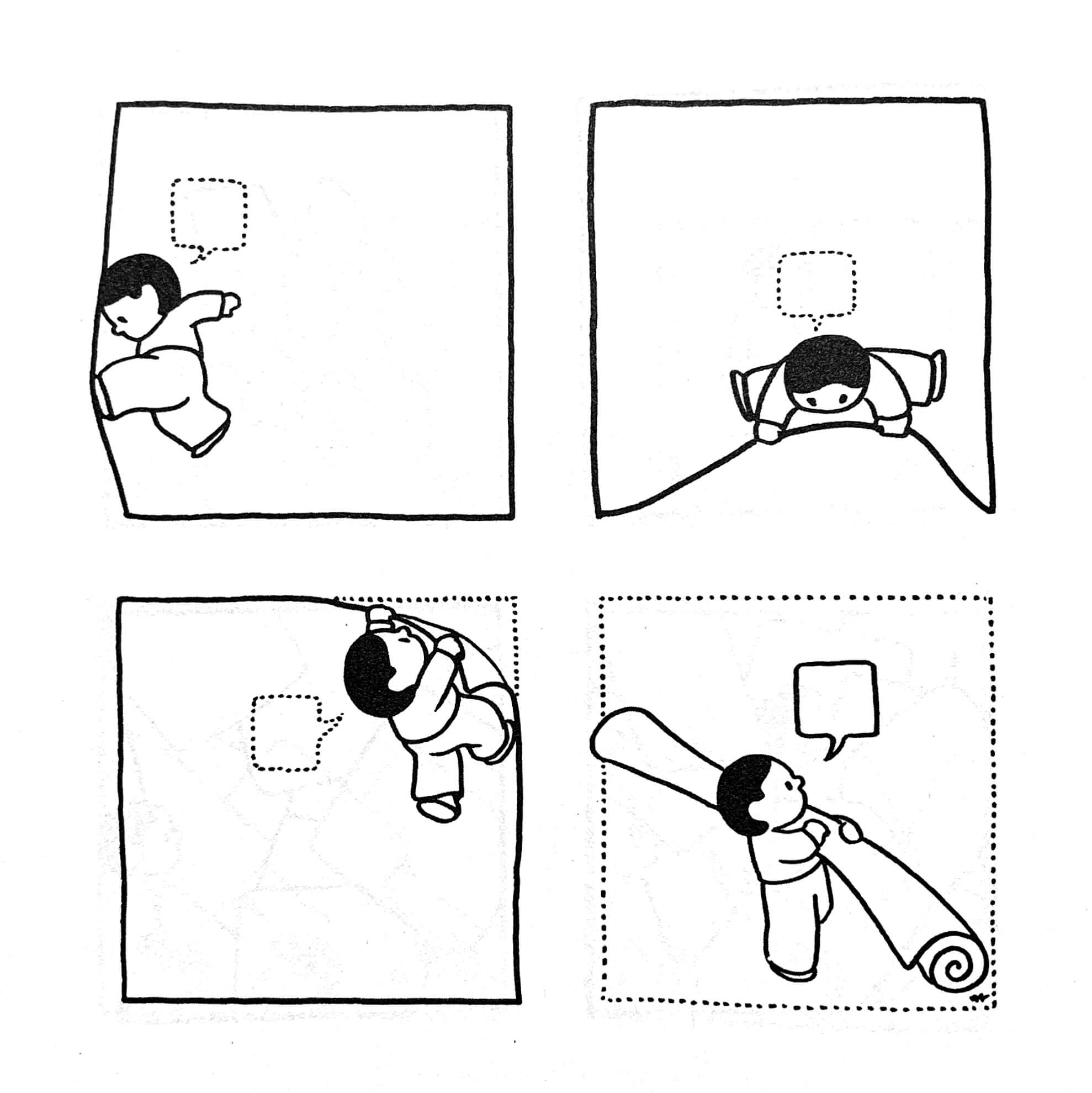7 12 月, 2020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纪念碑 —— 观《庚子惊梦》已关闭评论 § permalink
文/梁栋﹝LeungTong﹞
惊梦由纪念碑开始。我们看到一座英雄纪念碑,镜头由英雄的眼睛开始,拉远,移动,推近,最后落定在另一位英雄的眼睛上。英雄的眼睛,装进了什么?看见,是一种隐喻。纪念碑下,一名黑衣演员躺在舞台正中,据闻,纪念碑是他的公共艺术作品,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会从纪念碑上面摔下,同时被骂得体无完肤。伴随影像,我们听到一阵阵嘈杂之声,纪念碑下面的群众在议论什么呢?听见,也是一种隐喻。剧场在思考:
什么时候广场成为反面的教材?什么时候历史缺乏辩证的概念?
什么时候剧场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问题成为问题的开始?
什么时候群众成为反面的教材?什么时候广场缺乏辩证的概念?
什么时候历史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剧场成为问题的开始?
什么时候问题成为反面的教材?什么时候群众缺乏辩证的概念?
什么时候广场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历史成为问题的开始?
以上,既是剧场的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折叠成潜意识,潜入梦中,在历史的不同断面,反复出现。这是偶然吗?庚子年似乎总是多事压抑。庚子年的不平静,是天灾,是人祸,还是更深层的文化潜意识?
第二折,一曲《牡丹亭·山坡羊》把我们带入汤显祖身处的年代。没乱里春情难遣,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我们已难以想象那个遥远的年代,那时女性不自知的压抑。I can still fuck,I can’t keep fucking。白衣女演员的独白,把我们拉进现实。我顶得住/我顶下去/我顶住它/我顶到底/我顶不住/我顶给你看/我顶心顶肺/我顶他的肺/我一直顶/我顶到底/我顶不下去/我顶到底/我一直顶/我一直顶/一直顶。这是现代人的信念。近些年(一直以来)频繁发生的性侵案件、虐童案件、少年自杀案件,等等,很多时候,都是由「I can still fuck」(我顶得住)到「I can’t keep fucking」(我顶不住)的嬗变。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拒绝,不发声,不思辨,不改变呢。
在剧场,两个时空交错前行,我们似乎看到某些轮回,看到某些不自知的压抑在延续,某些被现代文明遮蔽了的文化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忽然,一声声痛彻心扉的哭叫,把我们带进一片荒野之中,那里有座纪念碑。舞台在重复第一折的影像,我们看到一座英雄纪念碑,镜头由英雄的眼睛开始,拉远,移动,推近,最后落定在另一位英雄的眼睛上。纪念碑在观看,观看历史沧桑之变。
我联想到「青山」。按中国的传统史学意象,「青山」与「青史」相配,「青山」也是历史的观望者、见证者。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一书写道:青山站在社会和自然的界线上,正因为青山的跨界存在,所以成为历史的理想证人。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青山必与流水合体,才足以隐喻不变与万变之道,不停的流水对应不居的世事,不移之青山对应永志之青史,「山水」代表了历史无限性的形而上尺度。① 那么,纪念碑呢?为什么我们要营造纪念碑,纪念碑是否同样代表了历史无限性的形而上尺度?渔樵是山水的有缘之人,山水无言,渔樵代之,言历史而不休。纪念碑无言,营造者安静地躺着,蒙面黑衣演员在他身上轻轻地盖上一面白布。
第三折,黑衣演员脱下面纱,徐徐掀开白布,发现躺在广场正中的,正是纪念碑的营造者。他如此惊讶,如此惊恐,可是他忘了,营造者身上的白布,是他盖上的。爪哇古典舞者缓缓来到广场中央,爪哇舞者是一个有趣的设置,他前后两张面具,似乎在暗示,蒙蔽着的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需要不同的标准面具/面纱以示人,我们都是「群众」的一员。黑衣演员随后坐在营造者身上,重新戴上面纱。什么是「群众」?按赵汀阳的研究,「群众」是基督教发明的概念,群众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乌合之众,而是在精神上有着高度相似性的一群人,他们只想,也只能,看到同样的自己,而看不到同样值得理解的他者。以此,上级阶层可以以精神为名制造出人皆此心的群众,建立一种以精神为依据的权威统治,通过建立对社会的精神文化领域的统治而最后统治所有心灵。② 然而,如赵汀阳所指出,群众只是「同」,却未必「和」,因为弱化了心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性变得单调而容易支配,却同时失去辩证能力与反思能力,因而无法真正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所以,当黑衣演员A不停搬弄椅子,试图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广场与纪念碑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能看清一切吗。当黑衣演员B几近癫狂地挥动手指,指着前方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吗。最后,他们和纪念碑营造者一样,倒在了广场正中。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太阳,总是相信权力需要中心。剧场提示,这是路易十四太阳王(复数)赐予大家的幻象。于是,「痴男怨女」们在断井颓垣桌椅间寻梦,在英雄碑下姹紫嫣红间寻春,但我们都知道,在牡丹亭移形换影的中心,在紫禁城从未惊梦的中心,你并没有爱我,你没有爱过我,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在虚虚实实的中心、真真假假的中心,在疯疯癫癫的中心、兜兜转转的中心、条条框框的中心寻找情欲,寻找权欲,到头来,会不会是一场竹篮打水?
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 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 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 俺的睡情谁见?/ 则索要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 迁延,这衷怀哪处言?/ 淹煎,泼残生除问天。(牡丹亭·山坡羊,昆曲)
Seasons came and changed the time / When I grew up I called him mine / He would always laugh and say /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play / Bang bang, I shot you down / Bang bang, you hit the ground /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 Bang bang, I used to shoot you down。 (Bang Bang ,Nancy Sinatra)
在剧场,两首曲/歌不断交替出现,意喻深远。四百年前,汤显祖以情爱书写挑战时代禁忌,「山坡羊」作为《牡丹亭·惊梦》中的一段曲词,铺排着当时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之情。「Bang Bang」作为电影《Kill Bill》的主题曲,轻唱着两性的美好与残忍。我们不禁想,情欲是否同构权力,谁是情欲的主体,谁是权力的中心?两性之间,家族上下,权力内外,背叛与服从,隐忍与抗争,欺骗与信任,意识与潜意识 …… 床第之欢与广场之痛有着怎样的隐秘结构?在剧场,在莫拉忧伤的旋律中,我们寻找伤风化床中术的魔幻中心、寻找示范淫行和行淫的界限、寻找欲迎还拒四处乱窜的公共空间、寻找颓垣败瓦良辰美景意淫的后庭风景、寻找残军败将欲海沉沦伤天败理剩下的枯枝败叶;在剧场,在一幕幕录像评议中,我们借以研究伤风败俗公然卖淫的风情、研究群交和杂交公民社会的高潮源头、研究我见犹怜一人一票前后夹攻的性交习俗、研究人尽可夫假智识分子摆出你上我下的民主姿势、研究无伤大雅牡丹亭惊梦的幽媾人文精神、研究残花败柳玉体横陈搔首弄姿的言论自由。我喜欢剧中这段文本,它给予我们无限思考。在某种意义上,情欲与权欲,是人性,是集体心智的一体两面。
第五折,在群众的惊恐与怒视中,纪念碑营造者用白布缠住自己的头,爪哇古典舞者缓缓来到广场中央,递给营造者一张面具,营造者将之戴上。营造者在独自言语:这里好像没有边缘 /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花园里面 / 我看不见花园有出口 / 我闻到很多烟雾 / 这个梦在剧场里面发生 / 我觉得四处有很多人 / 我只看到他们的身影 / 我听到很多枪声 / 舞台是不是花园 / 我好像看到你们 / 我是不是在做梦 / 我感觉自己存在 / 我站起来换个位置 / 我转头又看到你们 / 这个梦可以怎样完结。
第六折,一阵惊雷,庚子梦醒,营造者脱下面具,脱下缠绕在头上的白布,脱下黑色头巾,漏出本来面目。随后,他拿起面具,看着面具,戴上面具。一如第二折的白衣女演员,一直顶,一直顶,爬出象征权力牢笼的白桌子,随后又缓缓爬回白桌子。营造者在独自言语:这个梦可以怎样完结 / 这里好像没有边缘 / 我闻到很多烟雾 / 我在你的梦中 / 我转头又看到你们 / 我是不是还在做梦 /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花园里 / 我看不到花园有出口 / 舞台是不是花园。
营造者头缠白布的造型,让我想起勒内·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的艺术作品《情人》(Les Amants)。画中,一对情人头上蒙着白布,隔着布料亲吻。他们真的相爱吗?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然而,他们或许真的彼此相爱着,只是未能觉知自己曾蒙着白布,那是一份虚假的感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剧场中,这一面白布,这一张面具,是一种隐喻,而现实中呢,它会是什么?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不再看见,不再听见?令我们不再觉知,不再相信,找不到花园的出口?
丹尼尔·丹尼特在《心灵种种》描述了人类的四种心智:达尔文心智、斯金纳心智、波普尔心智和格利戈里心智。其中,格利戈里心智把他者的知识纳入自己的认知行为。我们终究是社会性的。他者的知识、经验、观念、思想无疑会丰富自己的认知经验,拓展思辨深度。然而,他者观念、传统经验、权力意志等等同样会被包装为某种意识形态,禁锢自己的思想认知。这点不得不察。例如,以乡土社会「教化权力」为核心的父权文化拒绝了每一个人的个性与成长,它复制着一幅幅遵从父权文化的面具,害怕思辨与充权,从而不断固化「教化权力」,也因此助长了文化主体的惰性。在父权文化中,我们把「识时务,识大局」(顺服)视为「成熟」,把「平庸」当作「常态」,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平庸让生命失去张力。再如,在强调平权的今天,女性仍然在用「男性眼光」来要求自己,仍然依赖传统加以的性别角色。现代女性虽然有了越来越强的女性意识及立场,却依然无法摆脱「男权思维」,反以男权的方式对待男性,甚至女性同胞。如是等等。往往,我们难以辨识周遭文化施加于我们的观念枷锁,而成为文化无意识中的一员。我们头上蒙着白布,未曾觉知亲吻的滋味。
2015年,Assemble Studio团队凭借作品《Granby Four Streets》成功斩获英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奖 —— 透纳奖(Turner Prize)。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Assemble带来的是一个街区振兴计划:通过跨领域协作、在地研究与商讨、以及不墨守成规的行事方式,以良善意念,藉由建筑设计与空间营造,与利物浦Granby Four Streets街区居民通力合作,改善生活空间,促成小型社会改革。有评论认为,Assemble Studio的作品让人们重新思考民主原义 —— 协作。本质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人与公共资源的关系,构成了政治/民主的核心要义。政治/民主就是在探讨这些关系的正当性,并以之建构社会。遗憾的是,民主原义被诸多以「政治正确」为名的政治实践所扭曲,渐渐限缩为选票、民粹主义、立场之争、诡辩、勾心斗角 …… 我们忘却了,「民主」本应藉由独立思考、辩证、批判、辩论而达成更为卓越的协作。
庚子年,新冠疫情肆意蔓延,以个体自由为名拒绝社交隔离是否是一种短见?我们如何在民主意志之下做出最优的公共决策,带来最大的公共福利?庚子年,逆全球化思潮重新抬头。庚子年,媒体评论环境越来越恶劣,各种反智言论盛行。我们能够因应公共空间面临的新挑战吗?如今,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显性权力,由技术、互联网、媒体、金融、资本等所构成的隐性权力正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无处不在,我们无处遁逃。多重权力之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可以肯定的是,失去独立思考与辩证能力的集体心智,一如头上蒙着白布,分不清淫行和行淫的界限。搔首弄姿的言论自由、人尽可夫你上我下的民主姿势只能带来群交和杂交公民社会的虚假高潮。
在剧场,在广场,在公共空间,我们是谁?扮演着何种身份?是公民,是人民,是群众?我们需要纪念碑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纪念碑?纪念碑在公共空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纪念碑承载了城市记忆、国族意志,在某种意义上,纪念碑以历史为精神权威,代表着一方意识形态。我们需要追问,纪念碑是否拥有历史无限性的形而上尺度?它何以启发后世?我们的文化以历史为本,而什么是历史呢?我们以历史为方法,又何以以史为鉴?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写道:青史变成如青山一样不朽的秘密在于:让事情变成问题,并且让问题永远成为问题,因此才能够以其永远在场的当代性去超越自身难保的现时性,永远作为未决问题而有必要理由永不退场。③
渔樵论古,把流水般的无常世事置换成没有定论的历史问题,进而构建一个可以不断征引的精神世界。在赵汀阳看来,这是渔樵的史学方法。书中,赵汀阳总结了渔樵史学三个基本性质:1)反思的对象是历史之道,而不是历史之事;2)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的历史分析,不以任何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为标准;3)不给定论而始终保持问题化,通过不休的谈论去保证历史问题常新在场。④ 无疑,渔樵史观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只有将历史化为问题与方法,我们才能避免在「造言大历史自欺盗铃」与「造言小时代浸淫情䧟」之间无限轮回。
人们喜欢将过往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记录下来以追忆、缅怀、寄托希望。在某种意义上,史册、纪念碑、剧场之「一桌两椅」,都创造了一个记忆的空间。我们会在记忆空间里面寻找什么呢。渔樵明白,所忆述之事如果没有构成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事迹就只能是笔迹,不能留存于精神世界而不朽,即便它产生了集体认同,成为集体记忆。纪念碑如是,剧场亦此。它们本应承载着一个无限开放的辩证的问题系统,而不只是限缩为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所以,什么时候历史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广场成为反面的教材,什么时候剧场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历史缺乏辩证的概念,什么时候剧场成为问题的开始,什么时候广场缺乏辩证的概念,什么时候问题成为问题的开始?
在剧场,人潮影像、浪潮影像反复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群众/公民的一员,我们都是浪潮的一份子,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必然指涉公共空间的方方面面。这两组意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剧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广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纪念碑」。在德国柏林汉堡街,有一座由艺术家波坦斯基创作的「空」的纪念碑。那是一座毁于二战的住宅,之后一直没有重建,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两座房子之间的空的空间。波坦斯基在完整留存的间隔墙面上放置了一块写着原住户姓名以及他们去世日期的牌子。这是「纪念碑」吗?没有英雄,没有伟大事迹,没有纪念实体。艺术家试图拓展纪念碑的深层维度:纪念碑可以是任何事物,纪念碑可以隐匿于城市的角角落落,但是,纪念碑所承载的种种问题,种种精神,应当勇敢地呈现于世人,让人们自由表达、质疑、反思、征引,成为思想资源。同时,纪念碑不应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单向度地为底下的群众灌输历史意识形态。
在德国汉堡,有一座由艺术家约亨·伽茨(Jochen Gerz)设计建造的反法西斯纪念碑。⑤ 这是一座12米高、表面涂了黑色铅层的铝制立柱,基座上面有一段用7种文字写成的说明,它邀请市民和访客在纪念碑上面签署自己的名字,以此,共同承诺对这段历史保持警觉。同时,这也是一个特别的装置,每当一段墙面刻满了字,纪念碑就会下沉一部分,1993年,纪念碑最后一次下沉,与地面平齐。如基座上的说明所述:「有一天它会完全消失,这里将会是一片空地。最后,只有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在这里,反对非正义。」除了人名,纪念碑上还刻满了各种涂鸦、污言秽语、反犹言论、弹孔等等,对于约亨·伽茨来说,这不重要,所有这些庄重的名字、粗俗的言语都是纪念碑的一部分,它真实记录了人们当下对于历史的态度,并随着纪念碑的下沉而封存于时间之中。在约亨·伽茨看来,坦诚地面对历史,反思当下这个时代,这才是纪念碑带给我们的意义。正如杨震所言:传统纪念碑很多都禁忌质疑和反思。但对于活着的人,对于历史更有意义的纪念,莫过于主动探寻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联,记忆不是沉埋在时间深处的黑暗石头,而是复活在当代意识和行为中的文化基因。⑥
第八折,在人潮与浪潮中,我迷失了。我们的世界已经不是「剧场」,我们的广场已经不需要「纪念碑」。可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终究还是要走出这个没有门口的走廊,走出这个没有出口的花园。我们需要在开始下堕之前醒来,而不是之后。
注:
①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三联书店,2019,p59
② 赵汀阳: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 第7期
③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三联书店,2019,p152
④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三联书店,2019,p154
⑤ 参考 张依玫:为了不忘却的纪念,卷宗Wallpaper公众号
⑥ 杨震:纪念碑的六种新建法 —— 德国公共艺术家约亨·伽茨介绍场,《雕塑》2013年 第4期
……………………………………………………
本文遵循 CC知识共享协议(署名/非商业用途/禁止演绎)。
《庚子惊梦》系荣念曾老师2020年剧场作品。相关作品见「进念·二十面体」油管频道。
25 8 月, 2016 § 谁之社区,为谁设计 —— 读山崎亮《社区设计》已关闭评论 § permalink
当社区逐渐取代村落,成为我们新的生活驻地,我们谈论社区,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社区(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语,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与吴文藻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Ferdinand Tönnies的著作时,创造了「社区」这一汉语词汇。尔今,社区概念日渐深入生活,我们有必要考察社区这一概念的文化意涵。当我们谈论社区,我们谈论的是乡土意识下的集体生活,还是现代背景下的公民觉醒?这点不得不察。
山崎亮在《社区设计》一书分享了他在日本的社区营造①的故事与思考。由于日本同样是以儒家文化构建社会基础,历史文化的相近,让山崎亮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在《社区设计》,我们可以读到东方社会如何开始自己的社区营造,以及社区设计所具有的潜力与魅力。
1.社区的当代性
2015年,一个平均年龄仅25岁的团队Assemble Studio凭借作品《Granby Four Streets》②成功斩获英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奖——透纳奖(Turner Prize)。这是透纳奖第一次授予一个团队/组织,第一次授予一个既非画作亦非雕塑的非传统艺术形式的作品。颇具争议,Assemble带来的是一个与利物浦Granby Four Streets街区居民合作的改善生活空间的街区振兴计划。人们疑惑,一个街区计划可以是艺术吗?它的当代性在哪里?
熟悉透纳奖历史的读者不会惊讶。1993年,雕塑艺术家Rachel Whiteread 以一座即将被拆除的维多利亚式老屋为模具,将其灌满水泥,并以这命名为《House》的作品俘获透纳奖的评委,同年,Rachel Whiteread获得了由 K Foundation 颁发的「年度最烂艺术家奖」。1998年,黑人艺术家Chris Ofili将大象的粪便加入颜料,以此作画,探讨外界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与种族困境,顿时舆论哗然。2001年,Martin Creed 凭借装置作品《Work No. 227: the lights going on and off》斩获透纳奖,据说当时一名艺术家曾愤怒地丢掷鸡蛋以示抗议。一间空旷的房间,里面灯光闪烁,这样的作品实在难以服众。然而,这就是透纳奖,永远在突破创作与艺术的框界,在世代的前沿施加它的影响力。
实际上,艺术介入社区已不再新鲜,艺术家们早已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艺术的扰动,带来社会的改变。在我们的意识里,社会改变往往关涉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然而,自Jean Lyotard以来,这种无所不包的叙事方式(按麦吉尔)备受质疑。Lyotard发现,宏大叙事往往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罗斯进一步论述,宏大叙事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因而必然是一种神话结构,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它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一直以来,在宏大叙事这一思维意识的影响下,市民被赋予被动的角色,主导城市发展的终究是政治与资本。这使得,如Alastair. Arvin所言,我们都把自己锁在这个工业时代关于「大」的怪圈里,认为能建造城市的只会是大型组织,他们将整个社区的塑形定性成为整齐划一的项目。③ 在经济奇迹之下,这一模式曾备受推崇。然而,当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民主实践开始遇到危机,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作为民主原义的人民权力变成鬼魅(按雷吉斯·德布雷),人们重新思考自己与城市的关系:我们把城市托付给资本,还是自己?市民应以什么样的角色介入城市建设?城市可以由市民主导建造吗?如果城市这一概念太大,那么,可以是社区吗?我们以什么样的角色、什么的方式参与社区事务?社会改变,可以是自下而上吗?通过社区实践,我们寻找那些被遗忘了的民主原义,进一步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生活的意义。这,就是社区的当代性。
黄宇轩如此评论Assemble的社区实践④:他们的获奖表明,当代艺术肯定了一种他们所象征的、反向的时代精神:改变世界需要的不是资本、宏大的理念或明星与领袖,而是跨领域的协作、在地的商讨和不墨守成规的行事方法。Assemble总是关注那些被遗弃的城市边缘街区,他们带着良善意念,通过在地研究,亲力亲为,与街区居民建立对话关系,通过建筑设计,塑造出不同阶层同时称颂的空间,通过社区营造,让公共性在这些街区再现,以渐进的方式,构建街区居民的自我意识,通过持续对话,探索现今群居共存的经济体系、社会议题,以及更多操作模式的可能及想象,以此促成小型社会改革。
约瑟夫・波伊斯认为,唯有艺术能够消解那些逐渐垂老并迈向死亡的社会系统之压制,去解构以建立一个如艺术品般的社会有机体。街区计划被视为时代艺术,意味着,当代艺术开始思考艺术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与社会生活的连结。事实上,这只是时代创新的一个缩影,在建筑、设计、公益、文化保育等领域,与Assemble类似的社区实践比比皆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便开始这方面的实践:以居民为主体,通过行政、在地居民、NGO、社会企业之间的协力合作,从硬、软两方面着手,解决地区、社区特定课题。社区营造亦成为日本颇具特色的地区治理模式。或许,在不远的未来,「社区」将成为一种方法论。
2. 激活社群主体的社区设计
2001年,应朋友之邀,山崎亮为有马富士公园研拟运营计划⑤,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有些极为讲究的公园,不到十年的时间便成为无人问津的冷清场所。山崎亮注意到,这些公园,无论当初设计得多么用心,在公园落成之后,设计师几乎不再过问,而运营者也只是关心公园的维护和管理。在比对一般公园和迪斯尼公园的管理模式之后,山崎亮发现迪斯尼公园在运营者/管理者与游玩的市民之间增设了一个新角色 —— 演员,迪斯尼的演员让市民与公园产生了有趣的连接。这一发现,让山崎亮意识到,除了空间的硬体设计之外,安排同乐活动的社群也十分重要,他在硬体设计伊始就逐步培育社群,并让周边社群介入公园的营造,不同的社群根据自己的兴致,策划出形形色色的活动,与游客分享公园的乐趣。这种居民参与型的公园管理模式让有马富士公园具有特别的活力。
随后,在儿童游乐园专案(2001)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园专案(2001 – 2007)⑦中,山崎亮延续了这种参与式设计。游乐场难道只能是大人设计给小朋友,不能由小朋友自己打造吗?山崎亮邀请未来最有可能使用公园的附近居民一起讨论心目中的公园形象,同时培训一批善于聆听的引导者,这些引导者与小朋友一起玩耍,引导小朋友创造游乐空间。通过游乐空间的设计,激活小朋友的想象与创造,激荡出新的游戏玩法,这些新的游戏又激励着小朋友创造新的游乐空间。建造游乐场的过程,让小朋友互相理解、共同学习、彼此协作,乐在其中。引导者、小朋友、居民慢慢形成新的社群,为公园的永续发展群策群力。
2007年,山崎亮继续深化他的社区设计理念。在泉佐野丘绿地专案⑧,山崎亮尝试改变公园使用方式与建造方式的关系,打造一座「边使用边建造的公园」,也即,先将公园的必要设施完善,然后由当地居民亲手打造公园。他们成立了「公园巡察员」、「公园俱乐部」等社群,这些社群成员须在荒芜的公园修建道路、游乐设施、表演空间,并举办自己想要从事的活动(森林音乐会、昆虫观赏会等),让游客享受公园的乐趣。社群的参与,让公园建造方式有了新的选择:我们可以用较少的经费建造公园硬体设施,而将大部分经费充实软体措施,支持更多的社群参与公园营造。
以上专案,不难发现,社群培育是社区设计的核心。山崎亮相信社群的力量,相信社群的活力能让社区实现积极改变。激发社群活力,重要的是,让社群成为真正意义的社区主体。在以往的社区建造中,人们往往将社区的未来交予建筑商、物业、政府机构,并把自己限制在有限的生活空间,不能够对社区的未来有所想象。山崎亮归还了居民的主体身份,恢复居民关于生活的想象力,让他们自行建造一个宜居的充满活力的生活空间。Assemble在Granby Four Streets及其他街区计划中,和山崎亮一样,他们提供街区居民一些不一样的愿景与想象,运用专才,将居民的想法变成具象的街区计划,同时让居民参与其中,一步一步地务实地实现。这也是山崎亮、Assemble和其他团队的最大不同,他们更尊重在地居民的意见,更善于通过社区社群凝聚力量,实现社区的永续发展。
3. 解决社会问题的社区设计
在山崎亮看来,设计(de-sign)是一种从讯息(sign)之中提炼精髓(de),并圆满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行为,他希望透过社区设计凝聚社群,以此解决人口老龄化,都市中心衰退,边际村落,森林问题,无缘社会等社会问题。2007年,余野川水库停建,国土交通省认为,无论从防洪蓄水的角度,还是未来对于这座水库的需求,水库都不宜兴建。对此,居民怒不可遏。当初,为了建造水库,居民将耕地、园林转让给国家,如今水库建造接近尾声,突然停建,居民一时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此前的振兴地区发展的硬体整建项目也被迫中止。在双方争执陷入僵局之时,山崎亮被委以重任。他让学生组成团队,开展「乡里探访」专案活动⑨,一方面,与当地居民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一方面,透过田野调查尽量发掘当地资源,编写资料,举办分享会,让当地居民重新发现当地的美好,共同探讨地区的未来。这些分享会让当地居民开始思考兴建水库及周边设施的必要性,同时引起政府的关注与兴趣。终于,政府机构、当地居民、社会组织放下过去的执见,坐在一起共同商议如何透过互助合作提高地方价值的方法。
2010年,某大楼建设公司计划在一建地兴建高楼大厦,他们不希望只由专家设计,而是想通过研讨会的方式将附近居民的意见纳入设计。建筑公司的态度足够诚恳,然而,附近居民却并不情愿,毕竟,新的高层建筑必然影响周边居所的视野以及部分居民的利益。山崎亮在听取众人意见后,提出「可以提升生活品质的共用庭院」的设想⑩,得到双方的认可。为此,山崎亮举办了三次研讨会,找出周边地区的特点及问题,讨论共用庭院如何利用,听取设计师对于共用庭院的设计构想。通过研讨会,探询附近居民的期望与意见,以此作为专家设计的重要依据,而当居民看到自己的社区愿景成为现实,无不欢欣雀跃。虽仍有部分居民持反对意见,但态度已有所缓和,愿意通过沟通、协调,完成共享庭院的共同愿景。
社区设计,可以通过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化解社会冲突。我想,这对现代社会有着重要启示。此外,在穗积锯木厂专案(2007) ⑪ 、震灾+design专案(2008)⑫ 、放学后+design专案(2009)⑬ 、issue+design专案(2010)⑭ 等社区实践中,山崎亮更清晰地意识到,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需要一套可以促使人们相互合作,并且凝聚社群力量的工具(设计)。如何透过设计提高社群的力量?该怎么制造人与人互相合作的机会?山崎亮与他的团队一直在尝试观察在地的人际关系、发掘在地的资源、努力厘清课题的结构,思索该如何搭配各项元素,促使在地的人们发挥力量克服自己面临的难题,并延续这份热忱。这也是山崎亮在社区设计中的基本模式。
4. 集体性,还是主体性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文艺展演、亲子活动、志愿服务走进社区,这些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社区生活。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我们的社区活动与其他成熟的社区营造仍有着相当的差距。不可否认,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络感情、融洽邻里的作用,但是,这还不足以展现现代社区的全部意义。特别的,这些活动在最后总是把社区精神归化为所谓的传统美德,这说明,我们对社区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的乡土概念。
一直以来,我们反复强调社区的「集体性」,而鲜少关注社区的「主体性」,这也就是我们与其他成熟的社区营造的差别。在山崎亮、Assemble等社区营造案例中,我们读到的一个关键字便是「主体性」。相较之下,我们的社区实践更像「社区服务」,而不是「社区营造」。社区营造的关键是「充权」(empowerment),它让一个社区具有永续发展的能力。Assemble的成功在于,他们不仅让那些被遗弃的建筑与街区空间焕然一新,而且与当地居民共同尝试构建街区的微型经济,通过成立社会企业,为社区社群提供更多的助力与机会,让街区居民在经济上拥有永续性与独立性。Assemble的社区创作虽以改善生活空间为目的,却有鲜明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关怀。他们十分重视与在地居民的对话,通过对话,一点一滴唤起群众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聚集更多积极能量,促成更多改变行动。
没错。社区,就是政治。曾经,人们错误地把政治等同于制度,或认为政治就是选票,这让民主原义渐渐被遗忘。事实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人与公共资源的关系,这些才是政治的核心要义。政治就是在探讨这些关系的正当性,并以之建构社会。社区营造,必然指涉居民主体、公共空间、公共资源,它让民主原义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这就是社区的当代意义。我们怎么营造公共空间?我们如何分享公共资源?「公共」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让个体与集体相互包容,而不是彼此对立?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终须回归「人」这一基本层面。可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长久以来的臣民意识及长者政治意识的影响下,集体往往被赋予政治正确或道德正确,于是,个体(人)被集体(社会)定义,因而失去主体性。我们总在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却没有意识到,没有主体精神的集体是空洞的,不尊重主体的大局是骗局。集体性与主体性并不矛盾,之间的微妙之处在于,主体性是基础,集体性基于主体性构建,反之则不成立。
如今,虽然乡土格局已然瓦解,我们却仍在用乡土观念(按费孝通)因应城市变化。城市,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林立的建筑、更多的就业机会、诱人的物质生活,我们还需要看见什么?在城市化背景下,社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社区?谁的社区?社区营造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义「公民」的涵义,Teddy. Cruz把「公民」理解为人们在城市空间重组社会规定的有创意的行为⑮。是的,to do is to be,公民主体性的成立,取决于公民行动。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日本先后经历了「诉求与对抗型」社区营造、「市民参与型」社区营造、「市民主体型」社区营造,由最初的历史城镇和传统街区的保护,到更为成熟的NGO运作以及更为自觉的市民行动,社区营造的空前发展,确立了社区营造过程中市民的主体地位。今日,我们同样面临老城改造等城市问题,如何开展文化保育,如何维护街区居民的利益,如何让居民以主体身份参与街区改造,进而培育具有现代意识的街区社群以及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社区?我想,我们需要思索。
5. 与日常同行
如果说,政治讨论的是人与人、人与公共空间、人与公共资源的「正当性」,那么文化所要探讨的则是这些关系的「价值性」。我们如何介入公共空间,我们如何分享公共资源,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什么的「关系」,我们可以蜷缩于私人空间吗。如赵汀阳所论述:生活的一切问题都是共在(coexistence)问题,如果像叙述事物的物理运动(原子化)那样去叙述生活的命运,生活的一切意义和价值将被取消,幸福的概念也将因此消失,因为没有一种幸福属于个体事物的存在状态 —— 幸福是一件事情,一件属于共在状态的事情。⑯ 于是,我们如何发现、如何创造一个可以令我们幸福的共在状态?我们何以共在,什么可以让我们联系在一起?
2001~2004年,山崎亮在大阪堺市环濠地区展开田野调查⑰,他们从「生活领域」、「生活空间」、「环濠动物园」三个方向出发,探寻环濠居民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居民日常活动范围十分狭窄,几乎没有和其他人的生活范围重叠,居民们更愿意自己窝在家里看电视、翻阅杂志。山崎亮让调研团队绘制《环濠动物园》地图,编制《环濠生活相关注解》、《环濠生活》等手册,同时培育出愿意让城镇变得更有趣的社群,以此一点一滴地改变当地的气氛,让居民可以扩展日常生活的范围,有更多的机会与人寒暄、闲话家常。2003~2006年,山崎亮开始另一项田野调查 —— 「寻找善用户外空间的人」⑱,他们发现经营小贩生意的阿姨、绿化铁路沿线的大叔、主动照料路旁植栽的阿姨等街区居民有着特别的本领,他们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妥善运用,为周遭环境带来正面影响。受此启发,山崎亮团队编辑出版了《OSOTO》杂志,刺激人们踏出家门享受户外空间,并因此孕育出善用空间的人/社群。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在山崎亮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我们忽略了「日常」,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日常」让我们联系在一起。可是,我们对日常的体验是真实的吗?日常空间激发了我们怎样的情绪?为探索一个有机结合的社区,德国艺术家Petra·Johnson策划了一个行为艺术项目 —— WALK WITH ME: COMPOSITION OF THE ORDINARY ⑲ :通过城市徒步、本地人与陌生人对话、地图绘制等方法来挑战大众心理对环境已有的认知,由此激发新的情绪(affect),进而探讨日常空间带来的共情体验。她在科隆和北京分别设计了行走线路,一条连接了一个小卖部和科隆大教堂,一条连接了一个小卖部和紫荆城。两条线路都是从一个小社区出发,最终来到城市的代表景观。Petra将行走线路等分成15分,设置了14个插入点,每个插入点都有相应的一张纸,每张纸有一个关于「日常」的提示,例如:观察一个日常行为,谁在做什么;列出一个不安的瞬间;指出你的认知和感受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差异;描述一个焦虑的瞬间 …… 每个同行者根据提示写下自己即刻的情感。这些情感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生成了日常生活的微小行为,陌生人和本地人的同行分享亦启发了诸多不可预期的对话。Petra将这些情感、这些对话记录下来,集合成册。每个不同的同行者的经历、经验、情感的重叠,产生了关于空间的流动认知。如Petra所述,正是情感照亮了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假设,照亮了我们耕耘城市景观的过程。
以情感和经验作为创作材料的还有Candy. Hang,她将附近废弃房屋的一面墙装潢成为一块巨型黑板,并漆上一句填空题:Before I die,I Want To_____。⑳ 每位路过的行人都可以拿起粉笔,写下自己的思考与愿望。很快黑板填满了字:在我死之前,我想种棵树;在我死之前,我想离经叛道;在我死之前,我想再拥抱她一下…… 这些日常情感的分享让社区空间具有建设性及启发性。在Candy. Hang看来,公共空间可以更好的体现到底什么对我们是真正重要的,无论是对个人来说或者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有了更多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希望、恐惧和经历,我们身边的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创造更美好的地方,更帮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技术与消费将我们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我们只活在一个抽象的时代现象里面,我们逐渐遗忘了生活的基本步骤,遗忘了时间,遗忘了空间,遗忘了「日常」。获得政治意义的主体身份并不足够,我们仍须获得关于生活意义的主体身份。在生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我们更需专注当下,回归日常,寻找更多有趣的连接,而社区将赋予我们新的契机,去遇见,去经验,去感受。
注:
① 山崎亮在《社区设计》前言部分对社区营造(Community Development)与社区设计(Community Design)做了简单说明,他认为社区营造的提法更为正确却十分拗口,社区设计则较为简洁,且意思相通。
② 参阅 http://assemblestudio.co.uk/?page_id=862
③ Alastair.Arvin:Architectur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TED.com
④ 黄宇轩:改变世界的方法——超越艺术和建筑的Assemble,立场新闻,2015/12/8
⑤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36
⑥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48
⑦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55
⑧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186
⑨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162
⑩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178
⑪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231
⑫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244
⑬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249
⑭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252
⑮ Teddy. Cruz:How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s migrate across borders,TED.com
⑯ 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三联书店,2013,P237
⑰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68
⑱ 山崎亮:社区设计,脸谱出版,2015,P81
⑲ 参阅www.walk-with-me.org.uk,或《城市中国》(2014.12)P18
⑳ 参阅www.beforeidie.cc,或Candy. Hang:Before I die,I Want To,TED.com
……………………………………………………
本文遵循CC知识共享协议(署名/非商业用途/禁止演绎)。
这篇文章是为广州湾书墟第九十一期「壹书壹会」而作。
文章授权刊载于公众号「广州湾青年会馆」、公众号「返屋企文化保育工作室」。